
风 荷
从前的荷花,和现在的没有什么区别,柔柔地醒在池塘。
我不喜欢在私家园林的水池里看荷,而喜欢在寂寥宽阔的水面上。那时候,我在杭州西湖边,与一枝荷,坐成平行的姿势。
夏天的荷花依然年轻,铺天盖地,长相恣肆。我时不时翻出那张旧照片,照片上有我趿拉着一双浅灰色的凉鞋,坐在湖边一块石头上,而那双鞋早已不知去向。
走过的一条路,会记住那里的标志。上初中时,为了抄近路,就走城郊结合部的农田小道,路边有一大片荷花,铺硕大的绿荷叶。
读过的一本书,会闻到里面的气息。孙犁的《荷花淀》,有大片大片的荷叶,粉色的荷花,文字里有荷婆娑的影子。
在中国的好多地方,你都有可能遇到一株荷。野外荷是成片的,一片荷,能构成一小块风景。荷丛中,有一群鱼,游来游去——荷在季节里生动。
只要有一掬水,就有舒展下去的理由。
上初中时,我就读的那所百年老校,图书馆山墙大殿合围的天井里,有一口荷花缸。正是盛夏草木忘情滋长的时节,荷醒了,从叶间钻罅而出,一枝独秀。陶质的水缸,裹衬着荷的亭亭玉立,陶仅用一缸水,就将荷捧在掌心。
汪曾祺种荷花,“每年要种两缸荷花,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,要瘦得多,节间也长,颜色黄褐,叫做‘藕秧子’。在缸底铺一层马粪,厚约半尺,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,倒进多半缸河泥,晒几天,到河泥坼裂,有缝,倒两担水,将平缸沿。过个把星期,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。过几天荷叶长大了,冒出花骨朵了。荷花开了,露出嫩黄的小莲蓬,很多很多花蕊。清香清香的。荷花好像说:‘我开了。’”
“叶上初阳乾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。”
《浮生六记》中记载夏月荷花初绽时,晚含晓放,“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之,香韵尤绝。”
荷叶下面是藕。周作人《藕与莲花》谈到莲荷小吃:“其一,乡下的切片生吃;其二,北京的配小菱角冰镇;其三,薄片糖醋拌;其四,煮藕粥藕脯……荷叶用于粉蒸肉,花瓣可以窨酒。”
我在西塘古镇吃荷叶包的粉蒸肉,油而不腻,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粉蒸肉是杭州一带的特色名菜,始于清末,相传用“曲院风荷”的鲜荷叶,将炒熟的香米粉和经过调味的猪肉裹包起来,蒸制而成。
荷在莲塘,积聚而生。季羡林《清塘荷韵》里说,荷在莲塘里会“走”。“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,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。我无法知道,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的淤泥里走动。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,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。”
我喜欢浅水荷塘这样清静的地方。有时幻想,在我的生活中,也有这样一片荷塘,一大片烦杂,包裹一小片安静。下雨天,可以打一把伞,到荷塘垂柳边漫步,听雨点打在荷叶上。天晴时,还可以邀上朋友于二,用干净的荷叶,包二两花生米、半斤猪头肉,坐在荷塘边喝酒。荷叶上有两颗水珠滚动;我和于二一边喝酒,一边谈诗:“荷,是一只摊在水面上的盘子,水天之间的容器,珠玉清气,包裹或者承托……”于二傻傻地地望着一大片摇曳的荷,说:“他现在不想写诗了,真想摘几片回去,煮一大锅荷叶粥。”
一个有着孩童般天真的男人眼里,荷塘是一个遮闭的世界,唯有一阵风吹来,荷在动,藕荷清香,正如古人所说,“风荷举——”。

青 苇
水做的植物,风一拨弄,即发出窸窣的天籁。这便是苇,青苇。
城市里看不到苇,往乡野走,夏日芦荡深处,一滴水汽凝结的露珠,像一滴汗珠,从光洁的苇叶上跌落。
那一年,三碗从乡下来。三碗是外婆的内侄,从小就没了爹,想在城里落脚,外婆收留了他。三碗在城里待了十天,他不习惯,要回乡下。
三碗带我去乡下。那个靠近黄海边上的小村庄,四周是大片大片的青苇。三碗的家,房顶是用苇片盖的,床上是用苇席铺的,门沿挂的遮阳、挡蚊虫的是苇帘,从里屋往外看,筛下稀疏的光影。就是从那时起,青苇便摇曳着我的童年。以至于一晃多少年过去了,我常梦见青苇,梦见我和三碗,划着船,在荷叶田田的芦苇荡里穿梭。
芦苇的青,是一种苇青,兀自的青。攥一把,一滴一滴的青汁沁在手心,有一种香。不知是谁说过,每个人都是一株思想的芦苇,立在风中梳理自己,我想起一些人,他们曾站在水边。
一株是孙犁,荷花淀里的那些芦苇,纵使被割倒了,捋成一片片,也会在那些水生女人的怀里跳跃。不一会儿工夫,“就编成了一大片,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,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”。
在孙犁笔下,苇是一种韧劲,一种柔美。“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、高大,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;正草因为有骨性,则多用来铺房、填房碱;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,却只能当柴烧;假皮织篮捉鱼用。”采蒲台的苇,如果贴上标签,制成凉席,摆到今天的商场、超市里去卖,指不定有不少“苇丝”。
一株是汪曾祺,《沙家浜》里的苇叶,在春来茶馆的窗后忽隐忽现。其实在写《受戒》时,汪曾祺借小和尚明子和农家少女小英子划船经过的芦苇荡,“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:‘哗——许!哗——许!’”。汩汩水声,似曾相识。等到若干年后,贾平凹到常熟一游,不禁感慨唏嘘:“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,和水中浩浩荡荡的芦苇。”
还有一株是德富芦花,名字中嵌入苇的影子,“带有泥巴的芦根处有小螃蟹在爬。在满潮的时候,一望无垠的芦花在水上映出倒影”;“芦间不仅是鲻鱼、虎鱼、虾等愿意栖息的地方,苍鹭、鹬鸟等也把这里当作隐身之所。”德富芦花的文字,隔着纸页,是扑面入怀的自然和乡野气息。
像青苇一样,秉性高洁的文人,擅长白描,峰岫尽头是白云,笔力穷尽,平淡是真。
有时候,摇曳的苇岸,还是一片爱情处女地。早先看琼瑶剧“在水一方”,“绿草苍苍,白雾茫茫……”,漫天芦花飞絮中,两个相爱的人,追风嬉戏。当时不免痴想,哪一天,与一个人在苇丛里携手而行?终不过是一场苇荡春梦。
夏日苇荡有一种遮蔽性,它契合少年的心思。乘一叶小舟,穿行在密密的苇丛中,隐韧的青苇,被船头挤倒,又爬起来,一个人的恣肆,只在他的内心汩汩流淌。
那年秋天,从乡下回来。三碗的来信便接踵而至,我念给外婆听:“在我最苦闷、彷徨的时候,是您给了我帮助……经人介绍,我认识了邻村的一个胖姑娘……冬天,要到海边去打苇,挣些钱,把房子修了,把亲订了,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……”三碗就像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,又像他家房前屋后的一株青苇,一个回乡知青,不向命运低头,又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许多人是苇,浸淫在自己的水边。有的人,跻身密匝匝的芦荡深处,绿浪翻滚,涛声回荡;有的人,只是孑然一丛,站在浅浅的水边,那里面,也有鸟儿栖息、做窝带来的简单快乐。
以天空为背景,勾画着旺盛生长姿势。我仿佛看到,青苇的根,鹰爪般四下里张开,紧攫膏泥。
那年的夏天,我的记忆,满是风中摇曳的青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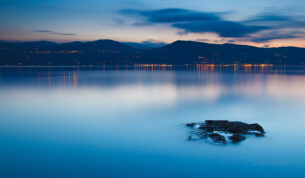
水 香
蒲棒上,立着一只蜻蜓。许是嗅着水的香气了,便振翅一飞,薄翼轻触水面,滑向湖的深处去。
水是有香味的。唐诗宋词里,李贺《月漉漉篇》:“秋白鲜花死,水香莲子齐。”读着这样的句子,鼻尖会掠过一缕幽幽草香。至于苏轼“闻香”知路程之远近,“水香知是曹溪口,眼净同看古佛衣。”嗅着湿漉漉的扑鼻水汽,一方水码头的繁华人烟,就在依稀不远处了。
洗过的湿漉漉衣裳,晾在绳子上晒,从一棵树,到另一棵树,水滴像一只座钟的钟摆,就这么一直嘀嘀嗒嗒,不紧不慢地敲颤着衣下的一棵草。这时候,阳光从布的经纬间穿透而过,待那些水滴声音渐渐停息,衣裳就干了,水的味道便留在上面了。
一小片水,是闻不到水香的。只有一大片,浩浩的生命之水,才散发出水体独有的香气。
儿时,我曾掬一汪水在手心。手掌心的那一汪水,有一尾小鱼,一摆一摆地颤动,手心间,痒痒的,“扑通”一声,掉进水里。那时,我陪父亲在一条大河边捕鱼,倾斜的河坡上,身后是一溜簇拥的斑驳树影,青草、野花、车矢菊,争挤到河沿边,四周氤氲着一片湿漉漉的水汽。
古人掬水闻香,河流的芬芳,混合着水中植物的清气。水面有荷叶、茭白、蒲草、菱藕、莲蓬,水边有茭白、蒲草、苦艾……河底,纠结着的水草,袅袅婷婷,不绝如缕,安静地躺在河底微微呼吸。水的味道,也就揉合了浸泡在水中各种植物草本的味道。有一段时间,我喜欢冲饮西湖藕粉,我知道,其实西湖水面是有限的,藕粉未必就出自西湖,卖的是西湖淡淡的水香。
在城市里,寻找水的潺潺流意,苏州城里有一条水香街。有一次,我站在古城的公交站牌下,看到这样的站名,想是小桥流水人家,户户尽枕河,站在石拱桥上,看远去逶迤的河道,临水小楼,那一扇扇木窗格,或开或合,窗下站着一个拿着绢扇的古代女子。窗子里面,不知发生过怎样的悲喜故事。
再往巷子里走,江南园林中有许多很美的亭子。一弯月牙状的水池,清澈见底,是专门用来亲近水的。《红楼梦》里有藕香榭,“四面有窗,左右有曲廊可通,亦是跨水接岸,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暗接……”,浮动的藕香,是水香的一种,闻着扑鼻的水汽花香,怡情养性。可见,才子佳人住在房子里,却常惦记着,这来自草木深处的素馨。
水边有着安静的故事。水之湄,适宜情人的款款散步。汩汩湖水拍岸,迷蒙的水气爽心、沁脾。饱含负离子,远离尘嚣、市侩的浑浊之气。月华如水的夜,风会把岸上植物的清新,吹送到水面上;那些流动的水,又把水的香味,一波又一波地涌到岸边。河水的吐故纳新,宛若一个女子,气息如兰的呼吸。淡雅的气质,由内而外,缓缓释放。
水香是河流的味道。我经常想起在乡间做客的那个夏天。傍晚,看到一个农人,撑着水泥船去湖的深处打捞水草。彼时,湖心往往有一轮倒映的天月。有着清冽的湖水是能够直接饮用的,撑船的人,从湖里舀一瓢清冽的水,咕噜咕噜,一饮而尽,腮帮边,有水溢出。
每一条有着淡淡水香的河流,会流向一座城市、村庄;每一条纯净的河流,总会流进一个人的心里。 |
 风 荷
从前的荷花,和现在的没有什么区别,柔柔地醒在池塘。
我不喜欢在私家园林的水池里看荷,而喜欢在寂寥宽阔的水面上。那时候,我在杭州西湖边,与一枝荷,坐成平行的姿势。
夏天的荷花依然年轻,铺天盖地,长相恣肆。我时不时翻出那张旧照片,照片上有我趿拉着一双浅灰色的凉鞋,坐在湖边一块石头上,而那双鞋早已不知去向。
走过的一条路,会记住那里的标志。上初中时,为了抄近路,就走城郊结合部的农田小道,路边有一大片荷花,铺硕大的绿荷叶。
读过的一本书,会闻到里面的气息。孙犁的《荷花淀》,有大片大片的荷叶,粉色的荷花,文字里有荷婆娑的影子。
在中国的好多地方,你都有可能遇到一株荷。野外荷是成片的,一片荷,能构成一小块风景。荷丛中,有一群鱼,游来游去——荷在季节里生动。
只要有一掬水,就有舒展下去的理由。
上初中时,我就读的那所百年老校,图书馆山墙大殿合围的天井里,有一口荷花缸。正是盛夏草木忘情滋长的时节,荷醒了,从叶间钻罅而出,一枝独秀。陶质的水缸,裹衬着荷的亭亭玉立,陶仅用一缸水,就将荷捧在掌心。
汪曾祺种荷花,“每年要种两缸荷花,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,要瘦得多,节间也长,颜色黄褐,叫做‘藕秧子’。在缸底铺一层马粪,厚约半尺,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,倒进多半缸河泥,晒几天,到河泥坼裂,有缝,倒两担水,将平缸沿。过个把星期,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。过几天荷叶长大了,冒出花骨朵了。荷花开了,露出嫩黄的小莲蓬,很多很多花蕊。清香清香的。荷花好像说:‘我开了。’”
“叶上初阳乾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。”
《浮生六记》中记载夏月荷花初绽时,晚含晓放,“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之,香韵尤绝。”
荷叶下面是藕。周作人《藕与莲花》谈到莲荷小吃:“其一,乡下的切片生吃;其二,北京的配小菱角冰镇;其三,薄片糖醋拌;其四,煮藕粥藕脯……荷叶用于粉蒸肉,花瓣可以窨酒。”
我在西塘古镇吃荷叶包的粉蒸肉,油而不腻,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粉蒸肉是杭州一带的特色名菜,始于清末,相传用“曲院风荷”的鲜荷叶,将炒熟的香米粉和经过调味的猪肉裹包起来,蒸制而成。
荷在莲塘,积聚而生。季羡林《清塘荷韵》里说,荷在莲塘里会“走”。“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,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。我无法知道,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的淤泥里走动。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,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。”
我喜欢浅水荷塘这样清静的地方。有时幻想,在我的生活中,也有这样一片荷塘,一大片烦杂,包裹一小片安静。下雨天,可以打一把伞,到荷塘垂柳边漫步,听雨点打在荷叶上。天晴时,还可以邀上朋友于二,用干净的荷叶,包二两花生米、半斤猪头肉,坐在荷塘边喝酒。荷叶上有两颗水珠滚动;我和于二一边喝酒,一边谈诗:“荷,是一只摊在水面上的盘子,水天之间的容器,珠玉清气,包裹或者承托……”于二傻傻地地望着一大片摇曳的荷,说:“他现在不想写诗了,真想摘几片回去,煮一大锅荷叶粥。”
一个有着孩童般天真的男人眼里,荷塘是一个遮闭的世界,唯有一阵风吹来,荷在动,藕荷清香,正如古人所说,“风荷举——”。
风 荷
从前的荷花,和现在的没有什么区别,柔柔地醒在池塘。
我不喜欢在私家园林的水池里看荷,而喜欢在寂寥宽阔的水面上。那时候,我在杭州西湖边,与一枝荷,坐成平行的姿势。
夏天的荷花依然年轻,铺天盖地,长相恣肆。我时不时翻出那张旧照片,照片上有我趿拉着一双浅灰色的凉鞋,坐在湖边一块石头上,而那双鞋早已不知去向。
走过的一条路,会记住那里的标志。上初中时,为了抄近路,就走城郊结合部的农田小道,路边有一大片荷花,铺硕大的绿荷叶。
读过的一本书,会闻到里面的气息。孙犁的《荷花淀》,有大片大片的荷叶,粉色的荷花,文字里有荷婆娑的影子。
在中国的好多地方,你都有可能遇到一株荷。野外荷是成片的,一片荷,能构成一小块风景。荷丛中,有一群鱼,游来游去——荷在季节里生动。
只要有一掬水,就有舒展下去的理由。
上初中时,我就读的那所百年老校,图书馆山墙大殿合围的天井里,有一口荷花缸。正是盛夏草木忘情滋长的时节,荷醒了,从叶间钻罅而出,一枝独秀。陶质的水缸,裹衬着荷的亭亭玉立,陶仅用一缸水,就将荷捧在掌心。
汪曾祺种荷花,“每年要种两缸荷花,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,要瘦得多,节间也长,颜色黄褐,叫做‘藕秧子’。在缸底铺一层马粪,厚约半尺,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,倒进多半缸河泥,晒几天,到河泥坼裂,有缝,倒两担水,将平缸沿。过个把星期,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。过几天荷叶长大了,冒出花骨朵了。荷花开了,露出嫩黄的小莲蓬,很多很多花蕊。清香清香的。荷花好像说:‘我开了。’”
“叶上初阳乾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。”
《浮生六记》中记载夏月荷花初绽时,晚含晓放,“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之,香韵尤绝。”
荷叶下面是藕。周作人《藕与莲花》谈到莲荷小吃:“其一,乡下的切片生吃;其二,北京的配小菱角冰镇;其三,薄片糖醋拌;其四,煮藕粥藕脯……荷叶用于粉蒸肉,花瓣可以窨酒。”
我在西塘古镇吃荷叶包的粉蒸肉,油而不腻,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粉蒸肉是杭州一带的特色名菜,始于清末,相传用“曲院风荷”的鲜荷叶,将炒熟的香米粉和经过调味的猪肉裹包起来,蒸制而成。
荷在莲塘,积聚而生。季羡林《清塘荷韵》里说,荷在莲塘里会“走”。“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,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。我无法知道,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的淤泥里走动。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,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。”
我喜欢浅水荷塘这样清静的地方。有时幻想,在我的生活中,也有这样一片荷塘,一大片烦杂,包裹一小片安静。下雨天,可以打一把伞,到荷塘垂柳边漫步,听雨点打在荷叶上。天晴时,还可以邀上朋友于二,用干净的荷叶,包二两花生米、半斤猪头肉,坐在荷塘边喝酒。荷叶上有两颗水珠滚动;我和于二一边喝酒,一边谈诗:“荷,是一只摊在水面上的盘子,水天之间的容器,珠玉清气,包裹或者承托……”于二傻傻地地望着一大片摇曳的荷,说:“他现在不想写诗了,真想摘几片回去,煮一大锅荷叶粥。”
一个有着孩童般天真的男人眼里,荷塘是一个遮闭的世界,唯有一阵风吹来,荷在动,藕荷清香,正如古人所说,“风荷举——”。
 青 苇
水做的植物,风一拨弄,即发出窸窣的天籁。这便是苇,青苇。
城市里看不到苇,往乡野走,夏日芦荡深处,一滴水汽凝结的露珠,像一滴汗珠,从光洁的苇叶上跌落。
那一年,三碗从乡下来。三碗是外婆的内侄,从小就没了爹,想在城里落脚,外婆收留了他。三碗在城里待了十天,他不习惯,要回乡下。
三碗带我去乡下。那个靠近黄海边上的小村庄,四周是大片大片的青苇。三碗的家,房顶是用苇片盖的,床上是用苇席铺的,门沿挂的遮阳、挡蚊虫的是苇帘,从里屋往外看,筛下稀疏的光影。就是从那时起,青苇便摇曳着我的童年。以至于一晃多少年过去了,我常梦见青苇,梦见我和三碗,划着船,在荷叶田田的芦苇荡里穿梭。
芦苇的青,是一种苇青,兀自的青。攥一把,一滴一滴的青汁沁在手心,有一种香。不知是谁说过,每个人都是一株思想的芦苇,立在风中梳理自己,我想起一些人,他们曾站在水边。
一株是孙犁,荷花淀里的那些芦苇,纵使被割倒了,捋成一片片,也会在那些水生女人的怀里跳跃。不一会儿工夫,“就编成了一大片,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,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”。
在孙犁笔下,苇是一种韧劲,一种柔美。“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、高大,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;正草因为有骨性,则多用来铺房、填房碱;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,却只能当柴烧;假皮织篮捉鱼用。”采蒲台的苇,如果贴上标签,制成凉席,摆到今天的商场、超市里去卖,指不定有不少“苇丝”。
一株是汪曾祺,《沙家浜》里的苇叶,在春来茶馆的窗后忽隐忽现。其实在写《受戒》时,汪曾祺借小和尚明子和农家少女小英子划船经过的芦苇荡,“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:‘哗——许!哗——许!’”。汩汩水声,似曾相识。等到若干年后,贾平凹到常熟一游,不禁感慨唏嘘:“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,和水中浩浩荡荡的芦苇。”
还有一株是德富芦花,名字中嵌入苇的影子,“带有泥巴的芦根处有小螃蟹在爬。在满潮的时候,一望无垠的芦花在水上映出倒影”;“芦间不仅是鲻鱼、虎鱼、虾等愿意栖息的地方,苍鹭、鹬鸟等也把这里当作隐身之所。”德富芦花的文字,隔着纸页,是扑面入怀的自然和乡野气息。
像青苇一样,秉性高洁的文人,擅长白描,峰岫尽头是白云,笔力穷尽,平淡是真。
有时候,摇曳的苇岸,还是一片爱情处女地。早先看琼瑶剧“在水一方”,“绿草苍苍,白雾茫茫……”,漫天芦花飞絮中,两个相爱的人,追风嬉戏。当时不免痴想,哪一天,与一个人在苇丛里携手而行?终不过是一场苇荡春梦。
夏日苇荡有一种遮蔽性,它契合少年的心思。乘一叶小舟,穿行在密密的苇丛中,隐韧的青苇,被船头挤倒,又爬起来,一个人的恣肆,只在他的内心汩汩流淌。
那年秋天,从乡下回来。三碗的来信便接踵而至,我念给外婆听:“在我最苦闷、彷徨的时候,是您给了我帮助……经人介绍,我认识了邻村的一个胖姑娘……冬天,要到海边去打苇,挣些钱,把房子修了,把亲订了,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……”三碗就像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,又像他家房前屋后的一株青苇,一个回乡知青,不向命运低头,又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许多人是苇,浸淫在自己的水边。有的人,跻身密匝匝的芦荡深处,绿浪翻滚,涛声回荡;有的人,只是孑然一丛,站在浅浅的水边,那里面,也有鸟儿栖息、做窝带来的简单快乐。
以天空为背景,勾画着旺盛生长姿势。我仿佛看到,青苇的根,鹰爪般四下里张开,紧攫膏泥。
那年的夏天,我的记忆,满是风中摇曳的青苇。
青 苇
水做的植物,风一拨弄,即发出窸窣的天籁。这便是苇,青苇。
城市里看不到苇,往乡野走,夏日芦荡深处,一滴水汽凝结的露珠,像一滴汗珠,从光洁的苇叶上跌落。
那一年,三碗从乡下来。三碗是外婆的内侄,从小就没了爹,想在城里落脚,外婆收留了他。三碗在城里待了十天,他不习惯,要回乡下。
三碗带我去乡下。那个靠近黄海边上的小村庄,四周是大片大片的青苇。三碗的家,房顶是用苇片盖的,床上是用苇席铺的,门沿挂的遮阳、挡蚊虫的是苇帘,从里屋往外看,筛下稀疏的光影。就是从那时起,青苇便摇曳着我的童年。以至于一晃多少年过去了,我常梦见青苇,梦见我和三碗,划着船,在荷叶田田的芦苇荡里穿梭。
芦苇的青,是一种苇青,兀自的青。攥一把,一滴一滴的青汁沁在手心,有一种香。不知是谁说过,每个人都是一株思想的芦苇,立在风中梳理自己,我想起一些人,他们曾站在水边。
一株是孙犁,荷花淀里的那些芦苇,纵使被割倒了,捋成一片片,也会在那些水生女人的怀里跳跃。不一会儿工夫,“就编成了一大片,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,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”。
在孙犁笔下,苇是一种韧劲,一种柔美。“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、高大,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;正草因为有骨性,则多用来铺房、填房碱;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,却只能当柴烧;假皮织篮捉鱼用。”采蒲台的苇,如果贴上标签,制成凉席,摆到今天的商场、超市里去卖,指不定有不少“苇丝”。
一株是汪曾祺,《沙家浜》里的苇叶,在春来茶馆的窗后忽隐忽现。其实在写《受戒》时,汪曾祺借小和尚明子和农家少女小英子划船经过的芦苇荡,“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:‘哗——许!哗——许!’”。汩汩水声,似曾相识。等到若干年后,贾平凹到常熟一游,不禁感慨唏嘘:“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,和水中浩浩荡荡的芦苇。”
还有一株是德富芦花,名字中嵌入苇的影子,“带有泥巴的芦根处有小螃蟹在爬。在满潮的时候,一望无垠的芦花在水上映出倒影”;“芦间不仅是鲻鱼、虎鱼、虾等愿意栖息的地方,苍鹭、鹬鸟等也把这里当作隐身之所。”德富芦花的文字,隔着纸页,是扑面入怀的自然和乡野气息。
像青苇一样,秉性高洁的文人,擅长白描,峰岫尽头是白云,笔力穷尽,平淡是真。
有时候,摇曳的苇岸,还是一片爱情处女地。早先看琼瑶剧“在水一方”,“绿草苍苍,白雾茫茫……”,漫天芦花飞絮中,两个相爱的人,追风嬉戏。当时不免痴想,哪一天,与一个人在苇丛里携手而行?终不过是一场苇荡春梦。
夏日苇荡有一种遮蔽性,它契合少年的心思。乘一叶小舟,穿行在密密的苇丛中,隐韧的青苇,被船头挤倒,又爬起来,一个人的恣肆,只在他的内心汩汩流淌。
那年秋天,从乡下回来。三碗的来信便接踵而至,我念给外婆听:“在我最苦闷、彷徨的时候,是您给了我帮助……经人介绍,我认识了邻村的一个胖姑娘……冬天,要到海边去打苇,挣些钱,把房子修了,把亲订了,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……”三碗就像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,又像他家房前屋后的一株青苇,一个回乡知青,不向命运低头,又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许多人是苇,浸淫在自己的水边。有的人,跻身密匝匝的芦荡深处,绿浪翻滚,涛声回荡;有的人,只是孑然一丛,站在浅浅的水边,那里面,也有鸟儿栖息、做窝带来的简单快乐。
以天空为背景,勾画着旺盛生长姿势。我仿佛看到,青苇的根,鹰爪般四下里张开,紧攫膏泥。
那年的夏天,我的记忆,满是风中摇曳的青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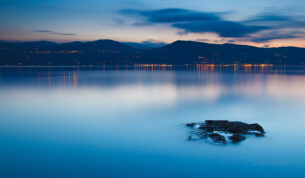 水 香
蒲棒上,立着一只蜻蜓。许是嗅着水的香气了,便振翅一飞,薄翼轻触水面,滑向湖的深处去。
水是有香味的。唐诗宋词里,李贺《月漉漉篇》:“秋白鲜花死,水香莲子齐。”读着这样的句子,鼻尖会掠过一缕幽幽草香。至于苏轼“闻香”知路程之远近,“水香知是曹溪口,眼净同看古佛衣。”嗅着湿漉漉的扑鼻水汽,一方水码头的繁华人烟,就在依稀不远处了。
洗过的湿漉漉衣裳,晾在绳子上晒,从一棵树,到另一棵树,水滴像一只座钟的钟摆,就这么一直嘀嘀嗒嗒,不紧不慢地敲颤着衣下的一棵草。这时候,阳光从布的经纬间穿透而过,待那些水滴声音渐渐停息,衣裳就干了,水的味道便留在上面了。
一小片水,是闻不到水香的。只有一大片,浩浩的生命之水,才散发出水体独有的香气。
儿时,我曾掬一汪水在手心。手掌心的那一汪水,有一尾小鱼,一摆一摆地颤动,手心间,痒痒的,“扑通”一声,掉进水里。那时,我陪父亲在一条大河边捕鱼,倾斜的河坡上,身后是一溜簇拥的斑驳树影,青草、野花、车矢菊,争挤到河沿边,四周氤氲着一片湿漉漉的水汽。
古人掬水闻香,河流的芬芳,混合着水中植物的清气。水面有荷叶、茭白、蒲草、菱藕、莲蓬,水边有茭白、蒲草、苦艾……河底,纠结着的水草,袅袅婷婷,不绝如缕,安静地躺在河底微微呼吸。水的味道,也就揉合了浸泡在水中各种植物草本的味道。有一段时间,我喜欢冲饮西湖藕粉,我知道,其实西湖水面是有限的,藕粉未必就出自西湖,卖的是西湖淡淡的水香。
在城市里,寻找水的潺潺流意,苏州城里有一条水香街。有一次,我站在古城的公交站牌下,看到这样的站名,想是小桥流水人家,户户尽枕河,站在石拱桥上,看远去逶迤的河道,临水小楼,那一扇扇木窗格,或开或合,窗下站着一个拿着绢扇的古代女子。窗子里面,不知发生过怎样的悲喜故事。
再往巷子里走,江南园林中有许多很美的亭子。一弯月牙状的水池,清澈见底,是专门用来亲近水的。《红楼梦》里有藕香榭,“四面有窗,左右有曲廊可通,亦是跨水接岸,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暗接……”,浮动的藕香,是水香的一种,闻着扑鼻的水汽花香,怡情养性。可见,才子佳人住在房子里,却常惦记着,这来自草木深处的素馨。
水边有着安静的故事。水之湄,适宜情人的款款散步。汩汩湖水拍岸,迷蒙的水气爽心、沁脾。饱含负离子,远离尘嚣、市侩的浑浊之气。月华如水的夜,风会把岸上植物的清新,吹送到水面上;那些流动的水,又把水的香味,一波又一波地涌到岸边。河水的吐故纳新,宛若一个女子,气息如兰的呼吸。淡雅的气质,由内而外,缓缓释放。
水香是河流的味道。我经常想起在乡间做客的那个夏天。傍晚,看到一个农人,撑着水泥船去湖的深处打捞水草。彼时,湖心往往有一轮倒映的天月。有着清冽的湖水是能够直接饮用的,撑船的人,从湖里舀一瓢清冽的水,咕噜咕噜,一饮而尽,腮帮边,有水溢出。
每一条有着淡淡水香的河流,会流向一座城市、村庄;每一条纯净的河流,总会流进一个人的心里。
水 香
蒲棒上,立着一只蜻蜓。许是嗅着水的香气了,便振翅一飞,薄翼轻触水面,滑向湖的深处去。
水是有香味的。唐诗宋词里,李贺《月漉漉篇》:“秋白鲜花死,水香莲子齐。”读着这样的句子,鼻尖会掠过一缕幽幽草香。至于苏轼“闻香”知路程之远近,“水香知是曹溪口,眼净同看古佛衣。”嗅着湿漉漉的扑鼻水汽,一方水码头的繁华人烟,就在依稀不远处了。
洗过的湿漉漉衣裳,晾在绳子上晒,从一棵树,到另一棵树,水滴像一只座钟的钟摆,就这么一直嘀嘀嗒嗒,不紧不慢地敲颤着衣下的一棵草。这时候,阳光从布的经纬间穿透而过,待那些水滴声音渐渐停息,衣裳就干了,水的味道便留在上面了。
一小片水,是闻不到水香的。只有一大片,浩浩的生命之水,才散发出水体独有的香气。
儿时,我曾掬一汪水在手心。手掌心的那一汪水,有一尾小鱼,一摆一摆地颤动,手心间,痒痒的,“扑通”一声,掉进水里。那时,我陪父亲在一条大河边捕鱼,倾斜的河坡上,身后是一溜簇拥的斑驳树影,青草、野花、车矢菊,争挤到河沿边,四周氤氲着一片湿漉漉的水汽。
古人掬水闻香,河流的芬芳,混合着水中植物的清气。水面有荷叶、茭白、蒲草、菱藕、莲蓬,水边有茭白、蒲草、苦艾……河底,纠结着的水草,袅袅婷婷,不绝如缕,安静地躺在河底微微呼吸。水的味道,也就揉合了浸泡在水中各种植物草本的味道。有一段时间,我喜欢冲饮西湖藕粉,我知道,其实西湖水面是有限的,藕粉未必就出自西湖,卖的是西湖淡淡的水香。
在城市里,寻找水的潺潺流意,苏州城里有一条水香街。有一次,我站在古城的公交站牌下,看到这样的站名,想是小桥流水人家,户户尽枕河,站在石拱桥上,看远去逶迤的河道,临水小楼,那一扇扇木窗格,或开或合,窗下站着一个拿着绢扇的古代女子。窗子里面,不知发生过怎样的悲喜故事。
再往巷子里走,江南园林中有许多很美的亭子。一弯月牙状的水池,清澈见底,是专门用来亲近水的。《红楼梦》里有藕香榭,“四面有窗,左右有曲廊可通,亦是跨水接岸,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暗接……”,浮动的藕香,是水香的一种,闻着扑鼻的水汽花香,怡情养性。可见,才子佳人住在房子里,却常惦记着,这来自草木深处的素馨。
水边有着安静的故事。水之湄,适宜情人的款款散步。汩汩湖水拍岸,迷蒙的水气爽心、沁脾。饱含负离子,远离尘嚣、市侩的浑浊之气。月华如水的夜,风会把岸上植物的清新,吹送到水面上;那些流动的水,又把水的香味,一波又一波地涌到岸边。河水的吐故纳新,宛若一个女子,气息如兰的呼吸。淡雅的气质,由内而外,缓缓释放。
水香是河流的味道。我经常想起在乡间做客的那个夏天。傍晚,看到一个农人,撑着水泥船去湖的深处打捞水草。彼时,湖心往往有一轮倒映的天月。有着清冽的湖水是能够直接饮用的,撑船的人,从湖里舀一瓢清冽的水,咕噜咕噜,一饮而尽,腮帮边,有水溢出。
每一条有着淡淡水香的河流,会流向一座城市、村庄;每一条纯净的河流,总会流进一个人的心里。